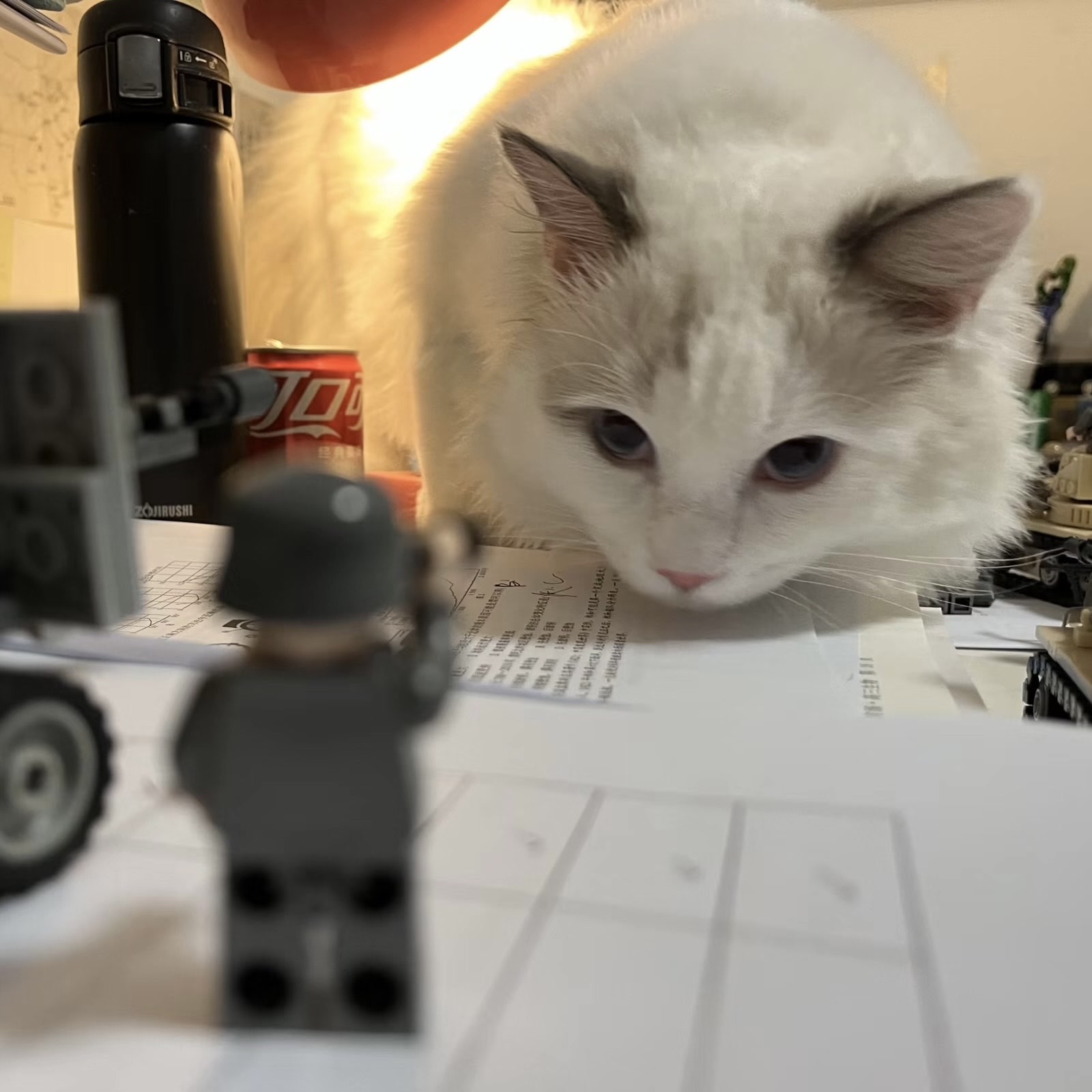纵火者
纵火者
本文为个人原创文章,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或引用。
午后的阳光宁静地出奇。十一月,在我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开始落叶,并且时常有寒风吹彻。我还清楚地记得高中里的梧桐树,落叶被秋雨打湿,天色灰蒙,光秃秃的枝干仿佛丧尽了生命力。但在这里,一个距离热带只差一个纬度的南方城市,十一月的午后竟然仍是一片郁郁葱葱。六月份的一张试卷把我带到了这里。从阳台向西南方望去,那是几株高大的棕榈,它们的树叶将整片的阳光抽离成丝。一片暖洋洋的懒意轻轻拥抱着我。我转头去看躲在枝叶之间的太阳。午后的一切都是金色的。
我享受这里的时光,享受被那种灿烂的氛围所感染,但我也明白这不宜久留,因为接触美好的事物越久,越容易使人怠惰,这种美好也就随之也会变为一种负担。往常,在点完一根香烟享受那惬意的五分钟之后,我就应该动身前往图书馆,要么看书,要么去应付我的作业。我不能让这份温暖安抚我太久,太久了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种侵袭。那是一种魔力,叫我度日如年。去图书馆是我逃避它的方式,那里总有学生在自习——做作业,准备考试或者研究课题。总之,很少的人在看书,仿佛对于那一整个图书馆来说,书只是她的装饰品。
这种看法显然是可悲的,但在这种可悲之中却鲜为人知地蕴含了它的精妙之处。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极少的人去光顾书架。而图书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成为了我自己的东西。
想到这儿,被午后的气息所感染的时间又将增加五分钟,但这一次我心甘情愿。我慢慢地让那种感觉包围我的头脑,然后缩紧。我感到所有事物都在放大。另一栋公寓楼上停着的白头翁的鸣叫,原本优雅而和缓,现在却仿佛成了一种噩梦中的回响。我的心跳加快,我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但我等待的事物又似乎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从我的公寓到图书馆需要穿越半座山峰。学校内部的隧道原本是一条公路,现在却被大学占为己有,甚至请学生在两边的墙壁上画满了壁画,已然成为一处景点。我每天下午就必须从这个景点内部穿过,百无聊赖地让我的剪影从壁画面前闪现过去。
隧道长达一公里,因此我选择了骑车穿行。穿过隧道,还需要经历一段长长的、路面极不平整的石板路。那仿佛是校园风景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成是文化,但骑自行车在上面将我平静的思绪颠得支离破碎。我并不痛恨它,尽管也会有许多游客在路旁摆拍,滑稽而又吸引眼球,但它毕竟只是差不多三分钟路程,三分钟之后是远离两旁行道树荫翳的平静,视野变得清晰明了。开阔的路面没什么美感,因此也少了许多游人。我可以好好地边骑车边想,到了图书馆,我应该先干什么。
“他们总是在那里,抱着电脑,或者摊开的草稿纸,俨然一幅工作者的姿态,”我总是在进门的时候想,“还有,别忘了每个人手边的咖啡。”
图书馆里总有一股很浓的香味。这种香味让我难以辨认。一般来说,我能轻易地认出某个人身上的味道,小苍兰、茉莉或者玫瑰的气味,或是清甜,或是浓香,有的时候甚至能精确到那个款式的名称。但在这里一切味道都被混合,这种混合让其中每一个味道都变得乏味。它,图书馆里的香味,应该也可以被赋予全新的名称,不过这个名称本身也必然是混乱不堪的。
在大学图书馆里,这是一种安静的混乱。人们都懒得知道别人在干些什么,我们只对我们眼前的任务感兴趣。在这里,没有什么奇妙的东西去组织,人们彼此断开潜在的联系。在黄昏的海滩上,那或许是落日余晖,又或是海浪拍岸,在公园里或许是葱茏绿意。但在这里,一个宁静的喧嚣地,没有一种动静去联系人们,唯一的可能——书架上的书本,在这里,甚至连一道景致也算不上。
“他们总是强迫自己去忽略,”我默默地想,“以获取更高的效率。”我很清楚我的目光现在是什么样——那估计是一种任何人看了都能对之深恶痛绝的眼神吧。
我上四楼的基本书库里去拿书,那里尽是些文学类的书籍。我走进书架之间,扑面而来的是书的气味——这里离那些混乱不堪的香味已经很远了。
“他们不应该呆在这里,”我望向册封上竖版的文字,目光掠过了一个又一个人名或书名,“他们可以去自习室咖啡店什么的。他们在这里仿佛是一群正在办公的人。”
“《暗店街》……”
我把那本书抽出来。二零一二年印刷的书,除了泛黄的纸页之外,还有一些二零一二年后的人的批注痕迹——它们是被用铅笔小心的刻画的。
我总有种感觉,感觉二零一二年的人们属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尽管那时我才不过十一岁,但这种感觉却异常的真实,有时甚至能找到证据,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些书里面的旁批。
有的时候我还能遇上一九八二年印刷的书,那种枯叶一般的黄色使我联系到的竟然不是凋敝的寒秋,而是绿意盎然的春天。它们的封皮是一张张简单的牛皮纸,侧边上用毛笔写下书名。那里时常有钢笔的印记,在那个时代,人们或许都还在用钢笔吧……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想用钢笔书写的?
我坐在地上书架之间的空地,直直地坐在那里。我只是翻了翻,草草地在每一页上搜出一句话来看了看,然后又把它从前往后翻了一遍,又从后往前翻了一遍,接着用大拇指揉揉书角,让书角的尖尖划过我指纹间的缝隙。最后我将它举起,念出它的书名、作者,摊开某一页,然后嗅了嗅。嗅的过程很短,我需要时长环顾四周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在注视着我的举动,我自认为那个动作是一种能够吸引人注意的行为。不过周围没有任何人,我嗅了第二次,然后接着环顾四周——还是没有什么人。我倒是挺希望有人能用异样的眼光观看我的行为,那对我来说甚至可以说成是一种特别的满足,不过很可惜,没人为我施舍那样的一瞥,因为周围根本没有其他人,他们可能都待在自习区或者研习区,而这里只是一片无人区。
“无人区,”我想,“那我算不算他们‘人’中的一个呢?”
我把那本书反复嗅了很多次,终于放回书架,我感到很满足。它的味道不亚于一款经典的香水。我又抽出另一本书几乎重复刚才的动作,接着把它凑到鼻子前面闻了又闻。有的时候,我也像动物一样干出一种标记领地的行为——我几乎把整个脸都埋了进去,这样纸页上就会沾上我脸上油和汗的味道。
和它们相处的时间总是愉快的。那里毕竟安静得出奇。如果能不别人发现(这是容易的,因为那里毕竟没什么人),并且藐视什么规规矩矩的话,那里一定是一个绝佳的幽会场所——昏暗的灯光,狭窄的过道,你甚至能听到情人间的心跳声。并不是每一个过道都设有摄像头,如果待在没有监控的过道里,那么只需要与那位情人一起享受肉体上的绝对自由即可。可我毕竟没有什么情人,我在这里只能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来自书的心跳声。
那个午后,阳光穿过玻璃映射在书架上,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我…”
“我”前面有两个音节,但我只能略微听清其音调,声母和韵母均无法分辨。我很好奇我听到的到底是什么。
“…/掉/我…”
阳光是一种让人产生光怪陆离的感觉的神奇之物。有时那种感觉也可以被直接定义为错觉。那个下午我或许产生了错觉,也说不定清醒异常。
我开始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可事实上,它们从四面八方传来,而且显然不是由一个东西发出的声响,而是一种诡异的异口同声。我真希望有人当天也在那里,并且也能听到那种声音。我被它包围,听得越来越仔细。我逐渐想起曾在什么地方也听过那种声音,那是在梦境之中。或者说,我现在只是在做梦?
我抽出一本书,用大拇指揉住它的书角。还是那种挠痒般的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我并不在梦中,这些声音也都真真切切。它们的确在我的耳边萦绕。
“烧/掉/我…”
这下我听得清清楚楚。这里唯一能烧掉的东西,除了我,就是这些书。“烧掉我。”这是这些书给我下达的指令。这是指令,一种命令!没错。而且我还随身携带着打火机。“这个图书馆竟然没有安检,”我想着,一边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作为引火的材料,我把它斜着吊在手上,这样可以让它烧得更快一些。“没有安检,什么东西都能带进来……”火苗已经窜上了那个小册子,然后饥渴地侵袭它的全身。那似乎是一种别样的快感,因为那东西在在发光,而且噼里啪啦的,像是在跳舞。“你看起来很快乐,”我把小册子扔到地上。四周书的声音越来越大,已经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诉求,甚至有些吵闹。“别着急,”我说,“会轮到你们的。”我又点燃了另一本小册子,因为那些吵闹声已经让我有些厌烦了,我需要提高效率,尽快地烧掉它们。不过,如果是平时它们就这样让我厌烦,我也就不会想来这儿了。我还是喜欢更安静的地方,而此时的它们像一群活蹦乱跳的麻雀。“吵死了!”我低吼了一声,为了是让它们都听得见——我在表明我的态度:如果接着这样吵下去,我就会拒绝它们的诉求,扑灭火焰,让它们安息在一团绝望的白烟当中。现在它们安静多了,我揣着手默默看着它们烧。它们倒是挺快活的,我却有些闷闷不乐。
因为我似乎清醒过来了,我在烧书。
建南大学图书始建于1930年。在此之后,将近九十年里,她没有遭到过任何的破坏,甚至幸运地躲过了战争。她的外观颇具海滨风情。旅游旺季时,无数的游客涌入校园,争相在其门口拍照——馆内是不允许游客进入的。图书馆内藏书众多,无所不有。其共有六层,每层设有学习区,但更大的面积还是用于摆放书架。
她于2019年被一场大火吞噬。大火焚毁了一切——书架、桌椅、建筑的木质结构,以及所有的藏书。大火也带走了一个人的生命,他被发现时已经烧得无法辨认。在尸体的旁边,人们发现了一小块别样的金属片,经鉴定,那东西属于打火机的一部分。但就此证据也无法证实那块黑炭即是先前的纵火者。监控探头没有拍到什么有价值的镜头,只拍到了白烟升起,火势蔓延,随后它自己也被焚毁了。
那天的火警响的很及时,除了那个可怜的人之外,其他所有正在自习的人都及时摘掉了耳机,逃出了正在燃烧的图书馆。
zeq 2023.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