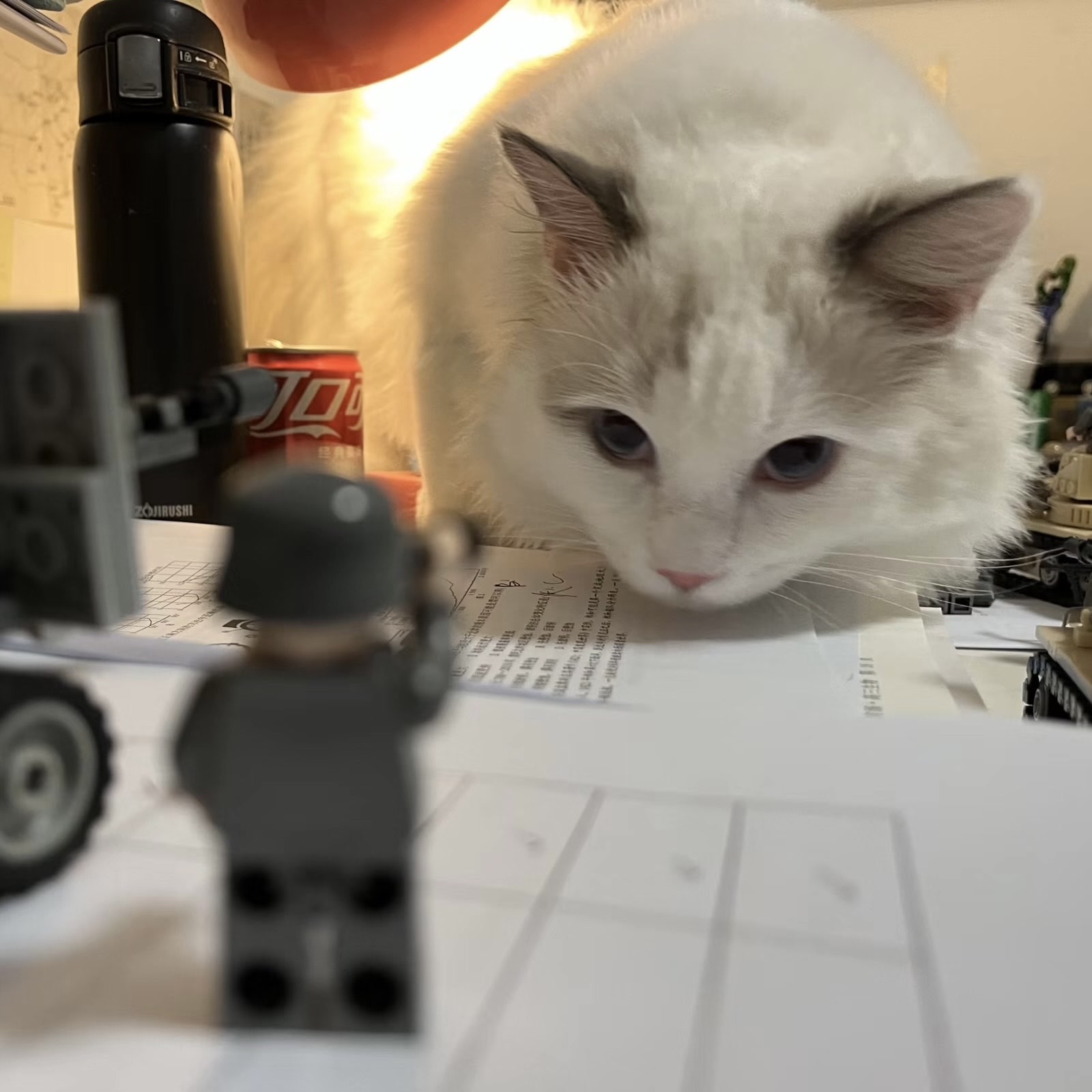深秋回忆录
深秋回忆录
本文为个人原创文章,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或引用。
蓝色的天井。这颜色与冷静渲染四周的空气。一只灰喜鹊的尸体像一块被人随意丢弃的垃圾一样横在四楼里厕所不远的走廊上。它被咬掉了头,直挺挺的,成为课间的一道奇观。
我们早就不记得那件事是哪天发生的,它明显是一个噩兆。在我们习惯了的认知里面,没有头的尸体是血腥的象征,更为可怖的是这份血腥就明晃晃的陈列的教学楼的走廊上。
那个时候,我们还喜欢在楼下的宣传栏里贴点什么,表达不满与控诉,有时被建议提出建议,最为经典的是二月的时候,校园里的一只猫受到了伤害,高年级的学长动手教训了两个低年级伤害猫者,被处罚。这件事被毫不留情地讨论,处罚结果被知晓的那一天宣传栏上热闹非凡,大字报、漫画、长篇社论应有尽有,同学们在上午大饱眼福。但神奇的是,一个中午过后,我们一觉醒来发现那里变得干干净净,留下几张寻物启事和一个丢三落四的人的校园卡,几枚失落的图钉挂在一边,上面还残留着纸角的碎片。这很快引起了众怒,有几个气不过的学生去找撕掉他们宣传物的负责人理论,得到“要保护施暴者”的回应。随后他们在各自的教室里慷慨地陈述自己的不满与厌恶,当然几周之后这件事情就不被人提及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擅长遗忘,有的时候甚至是遗忘自己所正在承受的苦难。教学楼五楼的厕所水压失调,导致有的时候冲不出来水,有的时候出水水压极大,于是课间总会有那么几个人见识到奇观。这奇观动静结合,蕴含着深邃的力量。他们先睹为快,然后津津有味地告诉班里的局外人。局外人们迅速赶到,效率如同总统被抓时赶到的记者。这时我们的同学们沉浸在这粗俗的快乐之中,甚至忘掉了臭味,忘掉了其他别的。
我们不想具体讨论这些。我们羞于讨论,认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认为这样的事情骂两句领导就行了,得一时口舌之快,然后赶紧去多做几个题。我们在初中的时候甚至上刚上高中时热心于结党结社,对抗不公,制定行动纲领,在根据个人喜好绘制党徽社徽,这一喜好在那时甚至可以称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高中一段时间后就消失了。我们开始更关心自己。
这对校方来说当然是好的 我从学校围墙旁的竹林间穿过,那是凄冷的深秋,露水沾在小径旁长长的绿得很深的草上。我从来不知道那种草叫什么,它们就这样理所当然地出现在竹林里,或者标本林里,给高大的植物当陪衬,却无名无姓。
学校里无穷无尽的植被,有些据说早有百年历史。刚开学那会,听退休的老教师聊,说标本林里的不少树都由职工之手,在首都沦陷前日夜兼程运往西南方,似乎这树就是学校理想的火种。那个时代的人还是很喜欢与需要谈理想的,现在也谈,只不过是在谈七八十年前那些人的理想,一遍又一遍地强化,说其永不过时。这倒也是真,因为那么多理想就没几个成为现实。理念还是理念,于是都懒得再提出什么新的理想,一句“某某说过:……”的话就能解决问题,何必再上去添油加醋呢?我们作为现代人实在没什么继续思考的必要。
我时常上课时看向那些标本林里歪歪斜斜的粗枝树干,平日里它们需钢管的支撑,就像病人身上插着的呼吸管。一到雨天那些枝干就会黑得更为深邃,像能吸收周围的颜色与情感。让人路过它们时沉默不语。它们身上都挂着牌子,写着树种、树龄,有的牌子是由铁丝缠上去的,铁丝勒进了树皮里,让人更加沉默了。当然这是在以前。从不知道哪一天开始,沉默成了稀有物。几个人顶着阴天路过标本林去小卖部,也要在路上造出一点声响来。
“啊!——”叫声回荡在树荫之下。鸟也懒得叫了。
我已经走到了那株紫荆旁边。它与我很久之前在南方看到的不同,是很小的一株,花也只是轻轻的一点紫,隐藏在竹林里。我估计这树不会有人欣赏,细细的枝条,挂着黝黑的豆子,即使是开花时也并不烂漫,更别谈引人注目。于是我将一部分灵魂分享给它,每次见它就像在镜中见到沉郁的人。
大师?真正的大师好像又不存在。对我来说,他们更像是世界伊始就已存在的故事,又接连着诞生出一部部作品。我不得而知。我只是个念高中的人。我不自觉地创造出作品,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小车库里的壁画,那是美术老师让我画的,我挑了一点喜欢的东西画在墙上。那地方照明极差,阴暗潮湿,画的旁边有一根水管,里面时不时渗出水污,所幸没污染到我的画。
其实我真正见到这些大师时会忍不住冷笑,盯着他或大或小竟然能够转动着的眼球,心想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没错,我坐在最后一排,离那家伙大概五十米左右,俯视他,就像在看戏,甚至看到这一出戏的内容也包含着前排的观众,我观察他们的举动,像一场游戏。
我在听他讲,就好像一个好孩子一样。上课请端正坐姿好好听哦 不过我开了一会儿小差。“讲得太虚伪!”我嗤之以鼻。
有时这个被称为“我”的家伙也会听他的话笑笑,觉得他文笔不错,接着又听了几句话。
“不行,讲的还是太他妈的虚伪。”
我们的诗意总是建立的太多人的苦难之上。
她的手指精致得像一件玉器。她在撩她的头发,香水味扑到我的脸上。那些杂音,甚至是我心跳声都被隐藏。隐藏吧,美的感觉。让美上台去取悦别人……
我从讲座出来下完楼梯,一抬头,一个刮了胡子的鲁迅从我面前骑着小电动车慢慢驶过。他的嘴角甚至有那种民国时候人才会有的微笑!
那种微笑,我觉得又似乎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一年半以前,在校庆画展,我盯着那幅“卅一年”的国画,画纸早已泛黄,但那肌黄之上似乎也浮现着那种微笑。我看着周围人的画,那些新人的画的笑声十分刺耳,仿佛进行着什么快乐的宣誓,宣誓作为一个创作者该受的名利。只有我的画早没了笑容。它被人一枪爆头,脑浆渗出来,流满整个天井。它的脸在抽搐,然后归于平静。
那画后来被挂在了实验楼的墙上——那具可怜的尸体。我大概在几周之后才知道这回事。我要去救它。
我擅自把它拿走,我知道这是会受罚的,即使作者是我。但现在我想不了那么多了。我最后看它一眼,那只不过是一副未完成的画罢了。我用每周二的下午的选修课为它构图上色,结果过了四个多月都没有画完。我精细地描了画面左侧的梧桐树,让阳光浮在它的上面,让树干没了老树的皱纹,而像一个新生儿一样平等。我把阳光撕碎洒在那片由歪七扭八的树木构成的标本林的林下。我的创作到了期限。我把它上交,那个根本没完成的东西,他们却说已经画完了,快交,校庆画展要用。我的画就是被这么处决了。
我在紫荆树旁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很奇妙没人看到我正在做什么甚至连一只鸟或者一只猫都懒得看他们就那样理所当然地从我身旁路过我试探性地窥探每一个路过的人或者动物看看他们是否在看我没有我把画放进那个坑里布面朝上再跪下来摸了摸它那是油画颜料凝固结块的颗粒感把土铲进躺着画的坑阳光再也见不到阳光。
zeq 日期不详(大概写于2024年上半年,因为现在即使你去实验楼也找不到那幅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