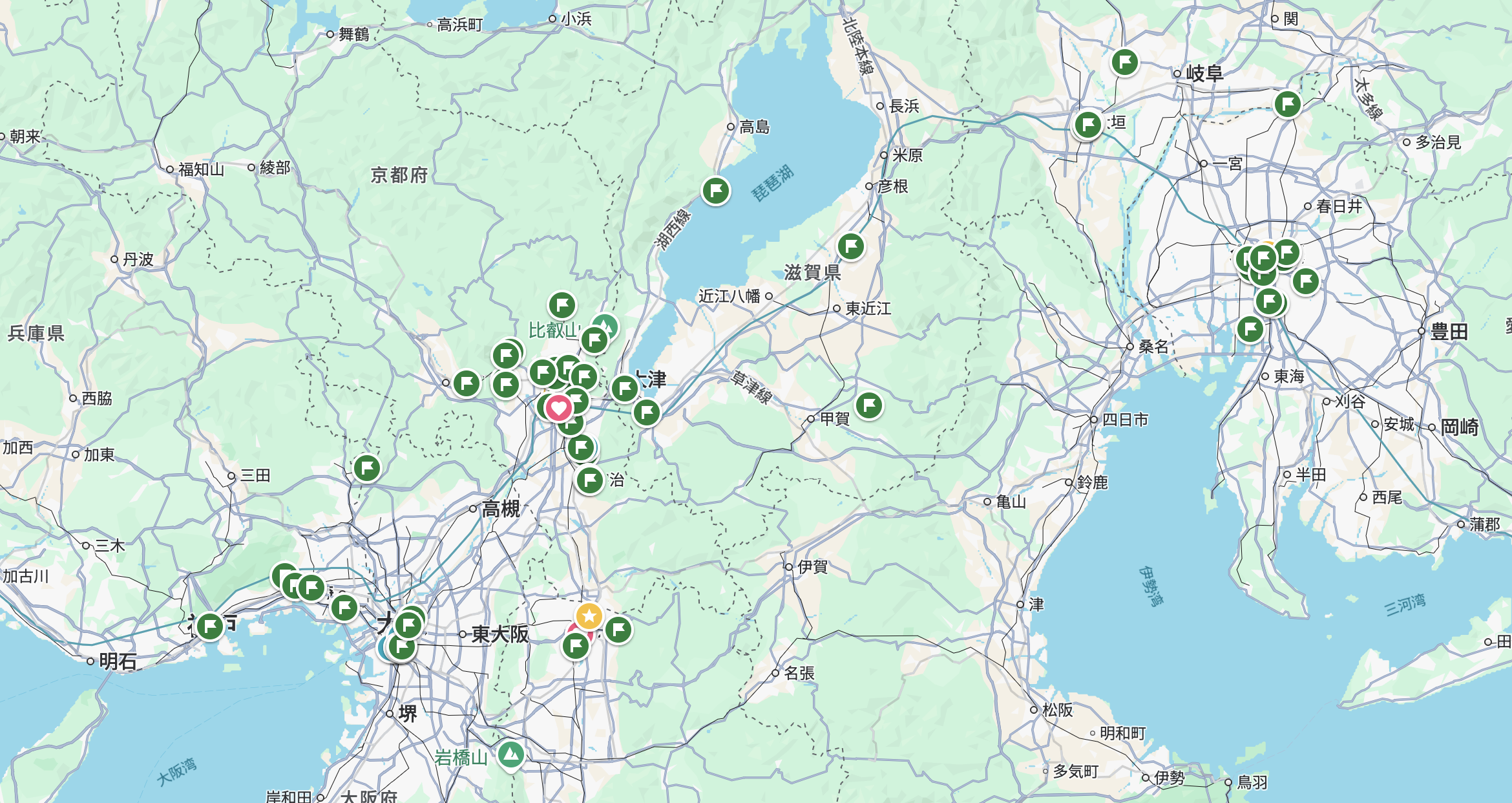美人
美人
本文为个人原创文章,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或引用。
这是一个春天,当天微微泛灰的时候,鸟儿都停在枝头,静静注视着屋里的一切。
我的社团老师走进我时,我已经在她的办公桌旁呆了十几分钟。在那之前我跟旁边的老师讲我是来找社团笔记的,他们信了。我找了半天总是找不到那个本子。为了那个本子,为了见到那个本子里边的人即使一眼,我已经策划了半个学期。我加入了一个我不愿进入的社团,与我不愿接近的人每周相聚一次,干着许多我觉得无聊透顶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一个人。
“你在这儿啊,”社团老师说。她是个将近四十多岁的高挑女人,说话时温柔而充满不懈,“我还以为你不来上课了。”
我没有回答,紧张着看着她的眼睛。我想着如何应答她接下来的话,她肯定马上会说:你在干嘛,在我办公桌旁干嘛……。她要是问这个,我就会回答说我是来……
“你是来找那个本子的吧,”她说着,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觉得我的心灵不懈一击,就这样被她看穿。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回答她,只能用沉默来应付周围老师异样的目光。我忽然觉得我所谓的计划在她这儿也许就是个儿戏,就是一个幼稚的冲动。一种耻辱感在我心中升起,搅着激动这个浑水,把我冲得头昏脑胀。
不过她先开口了。
“来找那个本子的,你不是第一个了,”她清淡地说。我像是受到她的目光的拉扯,抬起头,战战兢兢的看着她。等待我的却是一个微笑。
她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我连忙让了一下。抽屉里全是社团笔记的本子。有精致的线装本,也有直接用钉子订起来的纸。我感觉那抽屉里面是一片汪洋,刚刚我这是在这里苦苦地浮游,却怎么都无法寻觅的到。
她将一摞摞本子堆到地上,直到抽屉里只剩下一个纸页泛黄的皱巴巴的本子。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充满荆棘的城堡里的睡美人,等待着被哪个不要命的王子唤醒。它仿佛在散发着什么,灰黄漂浮着,融入周围不安的空气里。
我充满感激地从抽屉中将它拿出,接着用问询的目光看向社团老师。她的眼睛泛着奇妙而又柔情的微波,已经告诉了我一切。
在打开了神奇之物的最后一秒,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峰,我只记得那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它伴随着窗外传来的鸟鸣有节奏地跳着。我不知道我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我只知道再过一秒钟,一切心中的模糊轮廓都会变得清晰明亮,至于即将从朦胧的灰雾中走出来的那个身影,我也渐渐不在乎她的具体模样。在那最后一秒,我还保留着我的相信,以及我的直觉。我的泪水已经涌上了眼角。那个有着二十年阅历的本子也在同时被我打开。
半个学期前,在我刚进入这个高中之时,就有人对我说,学校里二十年前曾有个非常美的女生。当时我便好奇是什么样的一张脸值得被人铭记二十年。我便问那个传播消息的同学,有没有照片给我看看。她是这么回答我的:
“没有。我哪都找不到。你以为我没找过?我看了她那一届的毕业照。老实说,好看的有几个,但好看得像传说中那么好看的我倒是一个找不到。”
“那你知不知道别的?”我接着问。
“她是文学社的。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她笑了笑,说,“她简直就是一个传奇。没有人知道她是谁,长什么样,干过什么事,二十年了,所有人只说文学社有个女生非常美。”
我也快了地笑了一下。第二天报社团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了文学社。
这个社团里只有九个人,以及一位社团老师。第一节课上,老师毫不客气地问我们为什么报这个社团。有的人回答说喜欢文学,他们的脸上浮动着自负;还有人一边写作业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其她社团都报满了。
“看来只有我知道自己是来这里干什么的。”我想。
课程对我来说枯燥乏味。社团老师即不主动参与学生们的交流,也不提出指点。但她好像也不做别的,她就只坐在后排看着我们说话。我时常感到奇怪。我有时回头看她,她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她只是看着,没有视觉,没有听觉,也没有其她什么东西。但她一直都在看,从上课一直看到下课。我突然发现她空洞的目光里仿佛伸出手来在抓住什么,又或者是在试图寻找着什么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今天我趁她在看社团时溜出去,她也没有在意。我径直走向她的办公室。她在第一节社团课时曾说,本社从建设以来就有着写社团笔记的习惯,存档也在她那里放着。我知道这或许是个机会。
我翻到了那一页。那一页上有一张照片,是二十年前社团的合照。大概十几个人端正地站在那儿。
我的目光划过泛黄的纸页。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必须被认出来的人。
我仿佛心脏骤停。窗外的花香在一瞬间袭来,世界也全变成了一个点。她站在照片的正中间。我不敢想象她的美貌,每次看到她的脸,我就会把目光转移走。我尝试着忽略她。 “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问我自己。我不就是来看她的吗?照片中的她微笑着凝视着每一个见到这张照片的人,她似乎知道我的目光在躲闪,于是那笑便越发的柔美。渐渐地我克服了自己对她的恐惧,我试图在那一张脸上寻找到什么,但终究是一片空白。她只不过是个二十年前的人物。
我盯着那张照片,大概一共看了一分钟。一分钟后社团老师把那张古老的社团笔记合上。此时的我变得更加坚定。我仍然不愿意将我的视线从那神奇之物上移开。
“你们都是来找她的,”社团老师说,“我认识她。我和她一个社团。没错,都是在二十年前的文学社。她很美,对吧。”
我像抢似的从社团老师的手中夺回那个本子,又翻到那页。我狠狠地盯着那张照片,似乎尝试着再找出什么东西来。
我找到了上高中时的社团老师。是啊,她就站在正中间,就是刚刚我目光焦点的所在。我能认出来,纯靠下面标注的姓名。我留了一些时间给我的惊讶。
“那是你?”我问。
“当美变得绝对,一切都会开始荒诞起来,”她说,“不过这种绝对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我问。
她一个字都没有回答我,转身直接离开。
她留给我一个天大的谜。
我望向周围的老师,他们还在工作。敲击键盘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办公室里。他们中有一大半都带着眼镜,盯着屏幕,或者伏案改着卷子。中午的时候绝大多数老师都会睡觉,睡在那种可折叠的躺椅上。那种躺椅整齐地放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我身旁有一个长柜子,上面放着一摞摞试卷,这些试卷可能明天就会发给我们做,做完之后仍然要送到这里改。每个老师的办公桌上都乱七八糟的,各种基础学科或者是心理类的书籍码放在身后的大柜子上,而他们面前的办公桌上通常都是一个台式机,几个笔筒,几张相片,还有各种各样的试卷和作业。整个办公室被办公桌前的挡板隔成一个个小格子,每个教师就在这个小格子里面办公。无论教学楼是在上课还是在课间,这里永远都安安静静的。
这个景象对我来说很常见。我每天都要来这里送作业,我的老师批完之后我再把他们拿回去。可是此时,我手上的本子甚至都没有合起来,那美人脸上的眼睛还在对着我发笑!一阵不安像箭一样穿过我的心脏。那个本子好像燃烧起来,我的手感觉烫极了。我将本子甩出去,像是在甩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错,那些谜都被我解开了,都尘埃落定了。我此刻终于理解了社团老师眼睛,那一种似乎要抓住什么的眼神。我知道,要是我是她,面对问出来那个愚蠢问题的我,我也会转头就走。那种绝对已经不存在了,这本来就无需多问。
“所有人都只说她非常美。”我的脑中循环播放起这句话来。
我失魂落魄地逃离了那里。
(2022.5)